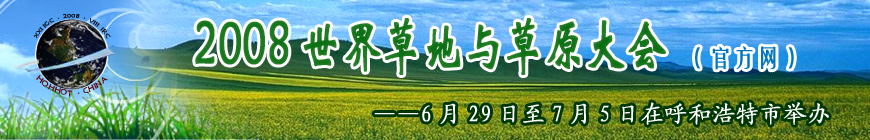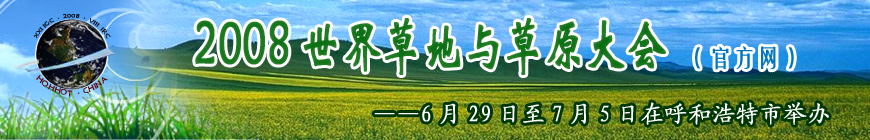一般认为,我国的草业发展始于20世纪初,但在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经形成部分草业生产的理论。中国草业的发展应先于大农业的发展,只是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草业甚至于畜牧业附属于大农业而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草业发展逐步加快,为此对我国草业发展的一些方面作简要回顾。
草业的初步发展
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大农业的发展,但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后,草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此前是草业的发展初期。
草业的萌芽
石器时代人类主要活动是采集、狩猎和捕鱼。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整个农业的萌芽,人类从利用天然产物逐渐转变为主动生产所需的生活物资。新石器时代促进整个农业起源的因素一是人口增多,二是猎物及自然产物逐渐减少,三是男女分工,女人定居并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植物生长规律,发现了农耕方法。这时牲畜对饲草的需要量远大于人类对粮食的需要量,因为饲养家畜需大量牧草,冬季缺草期尤需积藏,在积藏牧草场所中偶而发现牧草掉落的种子萌芽并生长,才无形中产生了栽培或农耕的观念。所以饲草业的历史先于农耕即大农业的历史[1]。
草业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以后是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000年-前700年),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饲草业及草地畜牧业的发展。圈养畜禽在商周时代非常普遍,圈养必然促使饲料生产的发展。商代已有“获刍”、“告刍”的记载。刍,甲骨文中用手取草之意。《说文》中“刍,割草也”,表明割草作饲料在我国商代已很普遍。马在商周时代成为重要的家畜,人们甚至不惜用秣(谷子)Setaria italica等粮食来作饲料。相传夏代就有“牧正”的职位,商代有管理王室马匹的“马小正”,有管理牧地的“牧”。牧地也有一套管理办法,《国礼》中有“牧师”一职,其职责是“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牧地由牧师分配给圉师,有计划地利用。“孟春焚牧”,据郑玄的注释是为了“除陈生新草”[2,3]。
由此可知,夏商周时代饲草业及草地畜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随后却停滞不前。
中国草业发展的停滞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草业的发展处于低迷时期,再也没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持续发展,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区域有所发展。
重农轻牧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饲养马、牛、羊、犬、猪、鸡、鹅、鸭,且已有畜禽舍及人工调制的刍料。但畜牧业的发展,已不如农耕发展的速度,也不如欧洲畜牧业发展的速度,人们保持重农轻牧的倾向,可能主要是受气候干旱、可食植物少的自然环境及只有贵族可享受肉食的社会环境因素的限制[1]。从此,草原畜牧业及草业逐渐变为大农业的附属,即使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饲草业曾有过一定发展,但却相对缓慢。
2•2草业的缓慢发展从战国后期起,中原的一些地区,骑兵逐渐代替兵车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促使历代封建王朝以养马业为基本国营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秦国开始用耕马,而汉代开始将牛作为役畜来使用,从而促进了草食动物的发展。秦汉时期,中国不但有发达的种植业,而且有较发达的畜牧业。汉代引入的苜蓿Medicago sa-tiva开始只在行宫别馆旁种植,《西京杂记》中说,风吹入苜蓿丛中,苜蓿花枝摇曳,放出光影,俨然在默默地照镜自赏,故苜蓿又称“怀风”、“光风”。因为发现马喜食,故推广到宁夏、甘肃一带,这对马、牛的品质改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饲草和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除种植苜蓿外,这一时期对其他青饲料的种植、收割和贮藏也颇为重视。《四民月令》中有正、七、八月种苜蓿,五、七、八月“刈刍茭”记载,“茭”就是青饲料。反刍牲畜如牛、羊,主要以放牧方式来经营,天气寒冷时补饲青茭(刍草)或干草。北魏时不仅有牧场,且已开始种植牧草,并且讲究豆科Glycine与禾本科Gramineae(杂谷)的混播,甚至不锄治杂草混作青茭(刍),或利用天然牧野。除牧草的栽培与管理外,还有牧野利用的记载。人们开始认识到牧草在抽穗至开花前宜刈作干草,并用最常见的大小豆萁来比较野草的营养价值。野生禾草中的芦(古时在开花前叫芦,花后成熟后叫苇)Phragmites communis,荻Miscant-hus sacchariftorus在其穗成熟前收获,以获取最高的饲草品质及产量。